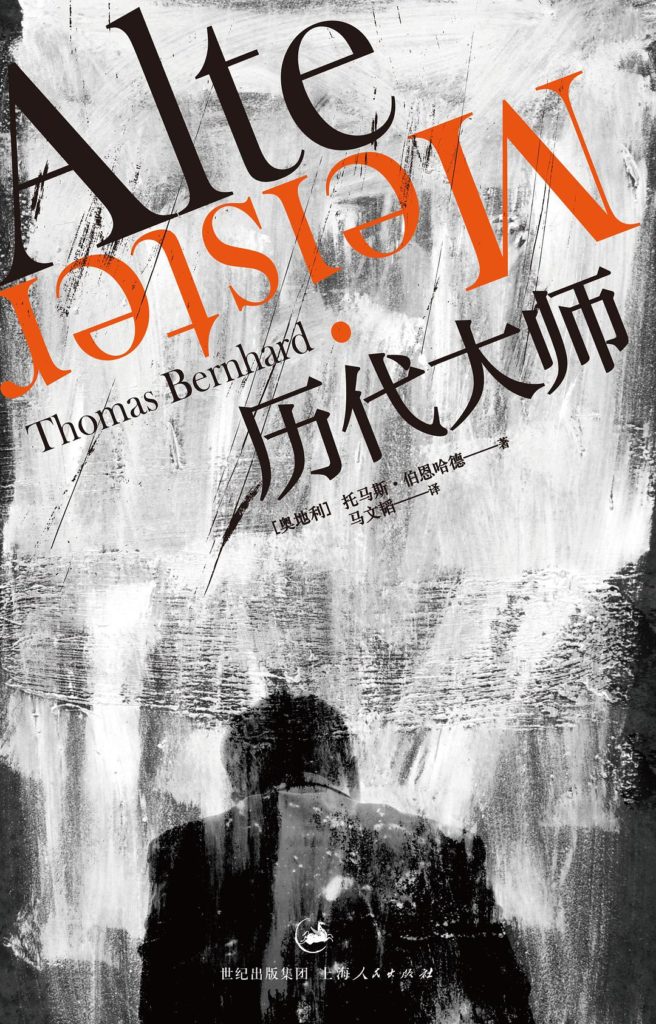 |
历代大师 托马斯·伯恩哈德 Thomas Bernhard 马文韬(译) B07L3PZVLX |
自从看了《英雄广场》的话剧之后,我对伯恩哈德的好感度倍增,这种对自己和社会深度自省的文风正好掐中我的软肋。稍微读了一点作者的资料,原来他自己可以算是一个拒绝诺奖的文学大师,我就把他作为这个月的大师作品阅读主题吧。顺便一说,《历代大师》其实有点《英雄广场》的影子,至少让我一下子get到了在看话剧的时候不怎么理解的对佣人的描写。
这本《历代大师》的名字很响亮,很早以前叶沙的读书节目就介绍过,我直到现在才读。故事讲的是叙述者的一个朋友,每隔一天都到当地博物馆独自一人坐在板凳上看一幅叫做《白胡子男人》的画作。几乎全篇都是这个朋友的话,抨击了几乎一切,包括历代艺术大师、奥地利这个国家社会。
一开始我有点受不了男主傲慢的口气,攻击一切自己还是要去博物馆是什么意思,就想看看他最后怎么自圆其说。没想到这个主人公竟然就是从头攻击到结束,你以为他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攻击了,他还是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攻击更多。闪光点是这本书解决了我正有的一些迷思,我现在的状态是觉得好的艺术作品我配不上,坏的艺术作品配不上我,觉得艺术作品是一种生活的逃离方式,又觉得是一种自我欺骗。书里面主人公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一个是在反击社会,另一个是在讨论艺术之于他的人生的意义。我得到的信息是,只有主人公那样的人上人才能拥有艺术或者艺术给他带来的东西,大前提是他懂,这些并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有这个天赋去懂的(包括他老婆)。世界以前分阶级,大多数的人日常平庸的生活作死作活去为高阶级的人提供接近艺术和幸福的供给,现在没有阶级,大家就算是逃离了温饱的束缚,有这个钱有这个闲但是也不能理解艺术因为没这个天赋。
这本小说行文的一大特点是男主的话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长,停也停不下来。好几个我想摘抄的地方,高亮要拉到最后,拉了半天我还没找到可以停下来的地方。真的是每一句话要么是循序渐进一步步往深处阐述的,要么是进一步扩张,前后关系紧密的。
下面是一些比较大段的摘抄。
艺术史博物馆是给我保留下来的、惟一的庇护所,为能继续生存下去,我必须到历代大师这里来,而且正是这些我早就,可以说几十年来就憎恨的所谓历代大师,归根到底我最憎恨的就是艺术史博物馆里的这些所谓大师,或者说所有的历代大师,总之一切称之为历代大师的人,无论他们姓甚名谁,无论他们画的是什么,雷格尔说,然而让我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正是他们。我走在这座城市里想着,我忍受不了这个城市,忍受不了这个世界,当然因此也就忍受不了整个人类,因为世界和整个人类已经可怕得让人无法再忍受下去了,至少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对于一个理智的人还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富于情感的人,这个世界和其中生活的人不久都是无法再让人忍受下去的了,您知道吗,阿茨巴赫尔?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和这些人中间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以及人类的一切都是麻木和迟钝的。他说,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麻木、迟钝,已达到一种像我这样的人所不能忍受的程度。像我这样的人不能跟这样一个世界生活在一起,像我这样的人不能够与这样的人类生活在一起,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麻木、迟钝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危险和残暴已达到了如此程度,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和在这些人当中几乎不可能哪怕是继续待上惟一的一天。雷格尔说,即使历史上那些最有远见的思想家也没有料到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叔本华没有想到,尼采没有想到,更不要说蒙田了,雷格尔说,至于说到我们最杰出的、我们的世界和人类最杰出的作家,他们关于世界和人类预言的和写的丑陋和败坏同现实的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最伟大的一位远见卓识的作家,笔下的未来也只作为可笑田园来描写,狄德罗也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可怕地狱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相比简直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今天我们所处的境况那才真是一想起来脊梁骨就冒寒气的地狱,狄德罗预言的和写的地狱也是如此,同今天我们所处的境况相比真是无所谓了。这一位从其俄国的、东方世界的立足点出发,如同其西方世界的对手,思想家和作家狄德罗一样,都没有预见、预言和预写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绝对是地狱的境况,雷格尔说。世界和人类今天达到了其在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地狱般状态,这是真情,雷格尔说。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作家,他们大家预见和预写出来的一切,与我们今天处在其中的地狱相比那简直就是安逸的田园,尽管他们认为他们描写的是地狱。今天的一切充满了卑鄙和恶毒,充满了谎言和背叛,雷格尔说,人类还从未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和阴险。我们可以观看我们想观看的,我们可以去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只有恶毒和无耻、阴险和背叛、谎言和虚伪,看到的总是绝对的卑劣。不管我们看什么,不管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要去对付恶毒、谎言和虚伪。如果我们到大街上去,如果我们敢于走到大街上去,雷格尔说,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谎言和恶毒,只能是虚伪和背叛,只能是最卑劣的卑劣。我们走到大街上就是走进卑劣中去,走进卑劣和无耻,走进虚伪和恶毒。我们说,没有比这个国家更虚伪、更恶毒的了,但如果我们走出这个国家,或者只是朝外边看看,就会看到,除了我们国家,外边到处也都是恶毒和虚伪,谎言和卑劣当道。我们说我们的政府是能想像出来的最讨厌的政府、最虚假的、最恶毒和卑鄙的,同时也是最愚蠢的政府,我们想的自然是对的,我们也随时去说,雷格尔说,但是假如我们从这个低劣的、虚假的、恶毒的和愚蠢的国家向外看,我们看到其他国家同样虚假卑鄙,总之同样的低劣,雷格尔说。但是其他这些国家与我们无关,他说,只有我们的国家与我们有些关系,因此每天我们都受到伤害,以致我们确实早已束手无策地生存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其政府卑鄙、迟钝、虚伪、欺骗,加之极其愚蠢。每天只要我们思考,我们就感觉到,管理我们的政府是虚伪、骗人的和卑鄙的,这还不算,而且是人们想像得到的最愚蠢的,雷格尔说,我们想到我们什么也不能改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只好软弱无力地一旁观看,这个政府如何越来越骗人,越来越虚伪、卑鄙和低劣,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手足无措地在一旁看着,这个政府如何持续不断地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不仅仅是政府虚伪、骗人、卑鄙和低劣,议会也是如此,雷格尔说,有时我觉得议会比政府还要虚伪、骗人,说到底这个国家的司法是多么虚假和卑鄙,还有这个国家的媒体、文化,归根到底这个国家的一切,在这个国家里几十年来充斥着虚伪和哄骗、卑鄙和低劣,雷格尔说。这个国家的确已经下降到最低点,绝对到了最糟糕的境地,不久就会放弃其意识、目的和精神。到处都在大谈特谈民主,简直令人厌恶!他说,您到街上去试试,您得不停地把眼睛、耳朵和鼻子堵上,您才能在这个实际上已成为公害的国家里生活下去。每天您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说,您都在越来越吃惊地经历这个国家的败落。这个国家的腐败,这个被愚化的民族的穷途末路。雷格尔说,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人们不进行反抗,雷格尔说,像我这样一个人对此每天都倍感痛苦。人们自然看到和感受到这个国家日益低劣和卑鄙,但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去抵制。政治家是刽子手,是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屠杀民众的刽子手,雷格尔说,几百年来,政治家们就谋害民族和国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我们奥地利人的政治家,雷格尔说,是最狡猾也是最没有思想的国家和民族的谋害者。政治家作为国家谋害者占据我们国家的最高位置,他们也把持着我们的议会,他说,这是事实。每位总理,每位部长都是国家的谋害者,同时也是民族的谋害者,他说,一个下去了,另一个又上来,他说,这位作为总理的谋害者走了,那位作为谋害者的总理又上来了,作为国家谋害者的这位部长走了,另一位又来了。民众总是只是被政治家谋害的民众,他说,但民众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虽然感觉得到,但他们什么也看不到,这是悲剧,雷格尔说。我们刚刚高兴地看到,这一位作为总理的国家谋害者走了,那另一位立刻就来了,雷格尔说,真是可怕极了。政治家是国家谋害者和民族谋害者,只要他们大权在握,雷格尔说,他们毫无廉耻地干着谋害的勾当,国家的司法部门支持他们卑鄙无耻的谋害,支持他们的卑鄙无耻地滥用权力。话又说回来,民众和社会有这样的国家自然是咎由自取,他们只配有谋害者作为政治家,雷格尔说。这是些怎样卑鄙、迟钝的滥用国家者,怎样的卑鄙、阴险的民主的滥用者啊,雷格尔感叹道。政治家绝对控制着奥地利,雷格尔说,那也就是说谋害国家者绝对地控制了奥地利。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此刻如此令人沮丧,只能让人夜不能寐,奥地利其他方面的状况也同样如此。如果您有机会与司法部门打交道,那您就会看到,司法部门是如何的腐败、卑鄙和低劣,还不说近几年司法中多得令人吃惊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周里不会在早已了结的案子里又发现审理过程中的重大错误,于是将所谓第一次判决推翻,以误判为其特征的奥地利司法部门最近几年误判的百分比很高,都是所谓的政治性的误判。雷格尔说,我们今天的奥地利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衰败的、魔鬼般的国家,而且有地地道道衰败的、魔鬼般的司法。许多年来奥地利司法就不可信了,其运行完全以卑鄙的政治方式,而不是照道理应该独立。谈到奥地利司法的不独立,那真是对真理的讽刺。今天奥地利的司法是政治性的司法,不是独立的司法。今天奥地利的司法的确是危及全社会的政治性司法,雷格尔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他说。司法在今天与政治沆瀣一气,您只要与这个天主教—国家社会主义的司法机构有接触,并且冷静地去研究就会明白,雷格尔说。奥地利今天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所谓司法审判失误最严重的国家,这是灾难。如果您同司法机构接触,您知道我本人就经常与它们打交道,那您就会发现,奥地利司法是危险的天主教—国家社会主义的压榨人的机器,驱动它的不是按照要求应有的公正,而是其反面,司法状况一片混乱,没有哪个国家的司法比奥地利的更加混乱、更加腐败、更加无耻和危及社会了,雷格尔说,不是偶然的愚蠢,而是蓄意的、卑鄙的政治目的左右着奥地利天主教—国家社会主义的司法,雷格尔说。如果您被带到奥地利法庭上,那您就只好受地道的天主教—国家社会主义司法来摆布了,那里黑白不辨,是非颠倒。雷格尔说,奥地利的司法不仅专横霸道,而且是碾碎人的机器,公正被荒谬的不公正磨盘碾碎。至于谈到这个国家的文化,雷格尔说,更加令人恶心。至于所谓历代大师,已经陈旧乏味,已经被吸干榨尽,已经售罄销光了,早就不值得我们去注意了,这您和我一样清楚,至于说到所谓当代艺术,如人们所说的,那是一钱不值。奥地利的当代艺术是如此廉价,都不值得我们为它脸红。几十年来,奥地利艺术家制造出来的都是浅薄煽情的烂货,按我的想法应该把它们扔到粪堆上去。画家画出来的是垃圾,作曲家创作出的是垃圾,作家写出来的是垃圾,他说。最臭的垃圾是奥地利雕塑家塑造出来的。雷格尔说,奥地利雕塑家的垃圾最臭,但却大受赞赏,他说,这就是这可耻时代的特征。奥地利当代作曲家总而言之都是小市民的调门追随者,他们那些音乐厅里的烂货臭气冲天。奥地利作家总体上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对其无法言说的甚至也不会写。今天奥地利的作家没有一个人真正会写,雷格尔说,他们编造出来尽是讨厌的、多愁善感文学的模拟之作,无非是为了让自己的钱包鼓起来,他说,无论他们在哪儿写,写出的都是垃圾,他们写施蒂利亚的、萨尔茨堡的、克恩腾的、下奥地利的、上奥地利的、蒂罗尔的、福拉尔贝格的烂货,并把这烂货无耻地、追名逐利地铲到书的封皮里。他们坐在维也纳基督教堂区的公用房里,或者在克恩腾州临时凑合着住的乡野村居里,或者施蒂利亚州的后院里,写他们那些废话,仿制出臭不可闻的、枯燥乏味的文学垃圾,雷格尔说,这些人装腔作势的愚蠢表演不堪入目。他们的书就是两代或三代人制造出来的垃圾,这些人从未学会写作,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会思考,所有这些作家写出来的都是枯燥乏味的模拟,其中的哲学思想是虚假的,所谓乡土文学是伪装的。雷格尔说,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令人讨厌的机会主义的国家作家,他们的所有作品都是抄袭的,他说,每一行都是偷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盗来的。这些人几十年来写的都是没有思想的文学,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出头露面,拿去发表也是满足他们的明星欲。雷格尔说,他们将他们的极端愚蠢的货色输入到电脑里,然后以这样的平庸乏味的蠢货获得各种各样的奖项。雷格尔说,假如我把施蒂夫特同今天这些从事写作的奥地利傻瓜相比,那么施蒂夫特还是很了不起的人物。虚假的所谓哲思和乡土情怀时下很流行,是这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所制造的愚蠢货色的主要内容。这些人的书不应送到书店,应该直接抛到垃圾场。总之,奥地利今天整个的艺术都应被抛到垃圾场去。歌剧院里演的是垃圾,音乐协会里的是垃圾,那些手拿锤子、凿子,傲慢无耻地称自己为雕塑家的人,实际上是些无产阶级卑鄙暴徒,他们的作品只不过是些大理石和花岗岩垃圾!雷格尔说,半个世纪以来总是这样一些让人沮丧的平庸之辈占据着艺术舞台,真是太可怕了。假如奥地利是一座疯人院也好啊!可是奥地利是一座医院,里边住的都是久病垂危的病人。老人在这里没有发言权,雷格尔说,年轻人更是如此,这就是今天的状况。自然所有这些从事艺术的人生活得都很不错,颁发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和奖金,不是这儿冒出一个名誉博士,就是那儿冒出一个名誉博士,一会儿这里戴上一枚荣誉徽章,一会儿在那里戴上一枚荣誉徽章,他们总是一会儿坐在这一位部长身旁,一会儿又坐在另一位的旁边,今天他们在总理这儿,明天在总统那儿,今天他们坐在社会主义工会之家,明天又在天主教的工人培训部里让人家赞颂和忍受他们。今天这些艺术家不仅在所谓的作品中是虚伪的,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们在生活中同在作品中一样虚假,雷格尔说。在他们那里,虚假的作品和虚假的生活不断交替出现,他们所写的是虚假的,他们的生活也是虚假的,雷格尔说。然后这些作家进行所谓作品朗诵旅行,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到处旅行,哪怕是与文学不搭界的感觉迟钝的小村小镇也不放过,他们从他们创作的垃圾中拿出一段朗读,让人称颂,让人把他们的钱包用马克、先令和瑞郎填满,雷格尔说。没有什么比所说的作家作品朗诵会更令人厌恶的了,他说,我觉得我最恨这种朗诵会了,但所有这些人到处去朗诵他们那些烂货,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归根到底没有人会在他们类似于四处抢劫的朗诵会上对他们所写的那一套感兴趣。可是他们就是要去朗诵,他们登台表演,向每位低能的市议员鞠躬,向每位头脑迟钝的乡镇首脑、每一位目瞪口呆的德语语文学者敬礼。他们从弗伦斯堡到博森一路朗诵他们的蠢货,毫不顾及廉耻地把这些臭气熏天的垃圾强加给听众。我无法忍受这种所谓作家作品朗诵会,雷格尔说,坐下去朗诵自己的废话,这些人朗诵的净是废话、垃圾。他们年轻时这样做还可以,雷格尔说,如果他们到了中年,或者快五十岁了,甚至超过了,那么这样做就特别令人反感。可事实上,正是这些上年纪的写手喜欢朗诵,雷格尔说,他们到处去读,或上讲台,或坐在桌旁,朗读他们写的烂货,朗读他们那迟钝的、衰老的文字。即使他们的牙齿不齐,已无法把握他们那虚假的词语的发声,他们仍然还登上随便哪一个市政厅的讲台,朗读他们那些招摇撞骗的胡诌八扯。雷格尔说,一个歌唱家演唱歌曲,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一个作家去表演自己的作品更令人无法忍受。雷格尔说,登上讲台朗读其机会主义的烂货的作家,哪怕是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他也只配是个流动剧团蹩脚的小演员。雷格尔说,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到处都有这样一些机会主义的蹩脚的小演员。是的,他说,如此看来怎能不让人对一切感到绝望呢。但是我努力不让自己对一切都感到绝望。我今年八十二岁了,拼命去抗争,不让自己对一切都感到绝望。他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可是不会永远都是这样。伊尔西格勒出现了,雷格尔朝他点头,仿佛想说,你过得比我好,伊尔西格勒转过身去,复又消失。雷格尔手撑在双膝夹着的手杖上说:您想想看嘛,阿茨巴赫尔,野心勃勃地要创作音乐史上最长的交响乐,这算什么本事。除了马勒没有谁会想做这种事情。某些人认为,马勒是奥地利最后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这很可笑。一个头脑完全清醒的人,为了挑战瓦格纳,让去掉五十名弦乐演奏员,太可笑了。雷格尔说,马勒使奥地利音乐绝对走到了最低谷。他的音乐纯粹是煽动群众的歇斯底里,他说,与克利姆特一样。希勒是更重要的一位画家。今天甚至克利姆特一幅很不怎么样的廉价煽情之作也可卖上几百万英镑。简直不可思议,令人反感。希勒的作品不是只图煽情,但是他自然也不是一个伟大的画家。像希勒那样水平的画家这个世纪里在奥地利还是有一些,但除了科科施卡没有哪一位是确实有重要影响的伟大画家。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伟大的绘画艺术。雷格尔说,我们艺术史博物馆这里有好几百幅所谓伟大的绘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觉得它们不再是伟大的,不再那么具有重要影响了,因为我们过分仔细地研究了它们。雷格尔说,任何我们仔细研究过的,在我心中便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们应该避免这样做,根本就不要仔细地研究什么。但我们实际上做不到,我们只能仔细地去研究。这是我们的不幸,我们这样做就把一切都给溶化了,把一切消灭了,我们几乎把一切都给毁灭掉了。歌德的诗行,雷格尔说,我们长久地研究,直到它不再如我们开始时觉得那么不同凡响,对于我们来说它逐渐地失去了价值,最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开始时我们觉得那是我们读过的最了不起的诗行,最后会让我们极为失望。一切我们仔细研究的最后都会让我们感到失望。运用分解和瓦解的程序,雷格尔说,早年间就对此习以为常,没有想到这乃我之不幸。如果我们较长时间去研究莎士比亚,那么他就会完全破碎了,他书中的句子就会让我们烦得受不了,人物形象在戏剧冲突前就已坍塌,会把一切都给我们毁掉。雷格尔说,最终我们对艺术根本就没有兴趣了,就像对生活没有兴趣一样,尽管它仍那么自然,因为我们逐渐丧失了单纯,随之也丧失了愚蠢。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拥有了不幸。雷格尔说,今天我绝对不可能去读歌德,去听莫扎特,去观看达·芬奇、乔托,现在我缺少这样做的前提条件。
当然我所以能以读叔本华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因为我为我的目的滥用他,的确以卑鄙的方式歪曲了他,雷格尔说,我把他完全作为我活命的药,事实上他与那些我上面提到的大师一样并非是让我生存下去的灵丹妙药。我们一辈子依靠那些伟大人物,依靠所谓历代大师,雷格尔说,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在您生命的决定性时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收集伟大人物、历代大师,以为在决定性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把他们派上用场,这也可以说就是为我们的目的滥用他们,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错了。我们用这些伟大人物和这些历代大师装满我们的精神保险箱,在生命的决定性时刻我们寻找他们的帮助,但当我们打开这精神保险箱,它空空如也,这是事实,我们站在空空的保险箱前看到我们如何孤单,如何确实一贫如洗,雷格尔说。人们一辈子在各个领域进行收集,最终仍是孤家寡人,孑然一身,雷格尔说,其精神财富方面也是如此。我收集了多少精神财富啊,雷格尔在国宾饭店说,结果还是空空如也。只是通过狡猾的伎俩我才能利用叔本华作为我生存下去的手段,雷格尔说。突然之间您懂得了什么是空空如也,您站在成千上万册书籍文章中间,它们完全抛弃了您,让您变成孤家寡人,它们突然变成了您周围这可怕的一片空虚,雷格尔说。假如您失去了最亲近的人,那么一切对您来说无不空虚,您可以随意往哪儿看,一切都是空虚,您到处望啊望啊,看见的一切确实皆为空虚,而且是永远的空虚,雷格尔说。您于是认识到,不是这些伟大人物,不是这些历代大师让您几十年维持生命,而是惟一的、您最爱的人。您有了这样的认识,在这样的认识中您就形影相吊,没有什么和谁能帮助您,雷格尔说。您闭门不出,陷入绝望之中,雷格尔说,您日益绝望,您每周都更加深陷绝望,雷格尔说,但忽然您从绝望中走出来。您站立起来,从这致命的绝望中走出,您尚拥有力量从这深沉的绝望中挣脱出来,雷格尔说,我忽然从朝兴格尔大街这边的扶手椅上站起来,从绝望中走出来,往兴格尔大街走去,雷格尔说,朝城内走了几百米;我从位于兴格尔大街这边的扶手椅上起来,走出家门,边朝内城走边想,现在只做惟一的一次尝试,一次生存下去的尝试,雷格尔说。我从兴格尔大街家里出来,心想,我再做惟一一次尝试,一次生存下去的尝试,怀有这样的想法朝内城走去,雷格尔说。这次生存下去的尝试成功了,很可能我在关键的、可能是最后的时刻从位于兴格尔大街这边的扶手椅上起来,走出家门来到兴格尔大街并走进城里,雷格尔说。然后我自然又回到家里,遭受一个又一个挫折,您可以想像到,这次生存下去的尝试不是惟一的一次,我还要做几百次这样的让我能生存下去的尝试,我一再这样做,从位于兴格尔大街这边的扶手椅上站起来,走到大街上去,确实来到人们中间,到这些人们中间去,最终使我得以拯救,雷格尔说。自然我问自己,我拯救了我自己,我这样做对吗?是否做错了?但是这已经是不相干的事情了,雷格尔说。我们迫切地想要随之而死去,然后则又不想这样做,雷格尔说,我生活在这样绝望的折磨中,您要知道,至今已经一年多了。我们憎恨人,然而又想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只有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中间才有生存下去的机会,才不会变得发疯。形影相吊的状态我们坚持不了多久,雷格尔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孤独一人生活,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离群索居,我们劝慰自己可以单独一人生活下去,雷格尔说,然而这都是梦幻。我们以为不与人交往没有关系,我们甚至以为,一个人没有我们也能生存,这都是幻想,我们只与我们自己在一起才有机会,只与自己孤独一人,这是异想天开。没有他人我们一点生存下去的机会都不会有,雷格尔说,不管我们能有多少伟大人物、能够有多少历代大师作为伙伴,他们都代替不了人,雷格尔说,最终我们会被尤其是这些所谓伟大人物,被这些历代大师抛弃,我们看到,我们受到这些伟大人物和历代大师的最卑劣的讥讽,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与所有这些伟大人物和历代大师始终只存在于一种讥讽的关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