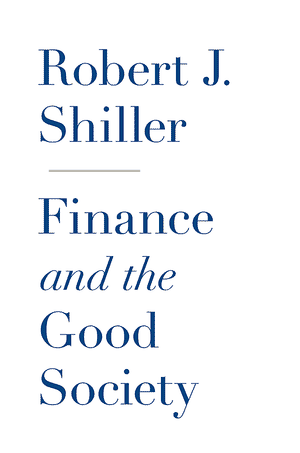 |
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
Robert J. Shiller B00C791JJI |
前不久我第一次完整地跟看完coursera的一个课程,就是耶鲁大学开设的《Financial Markets》。总的来说,这门课程是相当紧缩和高度浓缩的,它看问题的角度相对比较宏观。其中比较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讲到behavioral finance,所谓的经济社会我们经常用各种数学模型来阐述,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很不一样。可惜在这门课程里真正讲到behavioral finance的地方不多。然后我发觉原来这门课的主讲老师Robert J. Shiller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奖由这位Robert J. Shiller和另外两位Eugene Fama、Lars Peter Hansen分享的,评语是“for their empirical analysis of asset prices”。有意思的是另两位是很明显基于数学模型的(数学模型的一大假设是有效市场),而这位Robert J. Shiller则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所谓的行为经济学,几乎是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出发点了,感觉似乎是有效市场的纯对立面的了。于是我去读了作为推荐教材之一的Robert J. Shiller的一本书《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有中文翻译版本叫做《金融与好的社会》。
这是第一本我看序能看到如此燃的一本书!“好社会”感觉是那么遥远的一个词汇,好像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在思考的问题,但是其实在我们当今的社会,这一概念依然重要。那么金融和好社会又能扯上什么关系呢?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说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家们控制着,穷人永远不可能翻身。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这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吗?这其实是民主化(democratising)和人性化(humanising)的问题,所谓的democratisation of finance是指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for everyone;所谓的humanisation of finance是指taking account of human nature in financial plans and desig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再回到资本主义/金融的本质,其实是通过资本运作来分配资产,它本身并不是什么一部分人的利益工具。那么面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就并不是要去摧毁资本主义,而是要深化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再回想一下当代资本主义带来的东西,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其实是更多的公司被更多的人或机构以股权的方式拥有,这不倒正好是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吗?
序之后,本书分两部分,看第一部分的目录几乎就像是学财务学金融的工作指南,它列举了各种职业在金融世界的所作所为和面临的问题。我对于这个财务世界的理解是含混的。就好像有时买来一个新的科技产品,在不看说明书的情况下,对这个产品的总体理解可能足以支持使用这个产品。至于内部的原理是什么,各个部件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协作是什么,并不100%清楚,但是通过一些最直觉的推理,似乎可以大概理解一些。看了书以后,我似乎里清楚了一些思路,看到一些可以印证我以前初步想法的东西,也深刻感受到路途之遥远。我现在只看完第一部分,下面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总结和想法。对第二部分更是期待!
Part I: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 CEO
CEO最受攻击的点是工资太高。高可以被一种mechanism来解释,比如有一位能力很强的人才A做一家很烂的公司的CEO,工资是X,然后他通过各种努力把公司扭亏为盈并走上正轨,终于可以开始轻松一点了。然后另有一家公司,和原来的那个烂公司有着类似的问题,他们也想找类似的CEO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他们就去找A。此时的A不可能放下好不容易已经轻松了的活儿,然后去一家新的公司做更苦更难的活还拿X的工资。于是即便在新公司的扭亏为盈的活和老公司的扭亏为盈的活是一样的而当初做扭亏为盈的活的价格只是X,工资必然是上涨的。还有一个问题是,CEO的任命。如果不是那种自己创建公司的CEO,CEO的委派往往会有内部的关系因素,那何必不给个高薪呢?但是总的来说,作者不提议强制设定CEO的工资的上限,毕竟这可以被认作是一种市场行为,的确是有CEO就是值那个高薪的。
- Investment Managers
投资经理被攻击的点有两个,一个和CEO一样是工资太高,还有一个是他们其实并没有(不能)做到他们所宣称的高回报(主要是后面这个)。
到底投资经理管理的回报会比市场上的平均水平或者市场上的非积极管理的回报高吗?如果按照有效市场的理论,价格是对及时且对称的信息的体现,那么就没有道理有人能做的更好。但是要使得价格能够反应信息,那必然需要有动作的。也就是说,价格不可能自己去调整以反应信息,必然是有人(比如投资经理)去做了一些动作,比如信息的收集,交易的进行。这不就成了一种悖论吗?必须要有投资经理的存在,才会有有效市场;如果有了有效市场,就不需要投资经理了。
另外,对于投资经理来说,考核他们的一个指标叫做Sharp ratio,就是单位风险的额外回报。很直白的道理是,高风险高回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风险其实并不是持续的。比如说危险事件的发生概率是80%,但是其实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在一段(可能比较短的)时间内没有发生,然后才发生了。但是反过来回报却是看的到,可以真实计算出来实际值的。投资经理可以采用高风险的选项来追求高回报,而且只要他们在一开始就披露自己的策略,那么他们就不用为此承担什么代价。
- Bankers
这里指的是商业银行。银行家们被攻击的点有一点不一样,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脑子里只有钱。银行的作用有提供资金的流动性,它还给普通大众提供了一种代为投资的服务。商业银行往往在发展中国家里起比较大的作用,而在发达国家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弱。近期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所谓的shadow banks,这些银行打着投资银行之名在做只有商业银行才能做的事情,同时并没有接受相关机构的监管。这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源头。商业银行的未来和前景在于民主化,即建构面向更大众更穷人的银行服务。
- Investment Bankers
投资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帮企业发行股票的,要么即使IPO,要么就是seasonal offering。它的好处很明显,就是帮助“民主化”、“人性化”金融市场,使得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股票交易,其实和赌博差不了多少。我对上市这件事情也觉得非常疑惑,为什么大家都赶着上市要IPO。现在看起来,好像大多数企业上市的主要动机在于圈钱。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一家公司的价值就会平白无故地因为“上市”这么一件事情而翻个几倍。因为在我看来,所谓上市,只不过是把一家公司的价值用市场的眼光体现出来,等于只是一个评估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是一个外部的观察动作,怎么会改变该企业本身的价值呢?其次,所谓的股价到底体现的是这家公司的价值,还是在投资者心目中这家公司的价值,还是只是投资者之间的博弈的价格?我觉得应该是前两者,但是实际情况却似乎是最后一项,因为股价说到底还是供需关系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银行在做的事情就似乎不仅仅是帮助企业成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动作了。
- Mortgage Lenders and Securitizers
从定义出发,这里终于比较明显地涉及到了finance对good society的贡献。因为在good society里面,人们总是希望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家(一处房产)的。而这笔不动产的置办费用如此之大,几乎很少的普通人可以在不贷款的前提下企及。于是房贷抵押自然是帮助普通人可以买房的一个途径,帮助往good society走的一个途径。但是现在提到mortgage,那似乎成了美国公民的众矢之的,因为近期的经济危机就起源于次贷的崩溃。
这件事情的mechanism是这样的。首先,有三方参与买房的动作:买房者(借钱买房,并用房产作为抵押)、银行(贷款借出者)和政府(担保方)。在这个步骤上,其实就已经能看到一些矛盾,虽然这三方的终极目标可以说是一致的,就是为了让人拥有房子,但是这三方在对这件事情的考虑和时间纬度上是不一致的。第二步,是把抵押的这些房产,转化成由抵押支持的债券RMBS(Resident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y),这就可以直接卖给广大投资者。第三步,是银行会把这些RMBS再次打包组合,做成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分成不同的档次,依照风险回报分别出售。这一步就牵扯到了评级机构对于比较高档次的CDO的评级,事实上往往他们评高了。而最终崩塌的原因,是不管哪一步的参与者都共享了一个前提假设即“房价不会跌”。也就是说,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主要是系统上,而在于这个系统的参与者的默认假设。
我觉得这一章不仅说的有道理,而且很有警示作用。我觉得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是因为房价跌了;而中国的房产市场的泡泡那么大,已经不仅仅是跌那么轻易了。人家美国就好像是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缩了变矮了,而中国现在根本就是踩着高跷在云里,跌起跤来是摔死的节奏。但是现在中国人的心态大多是房产泡沫如果破了,那肯定什么经济就都崩溃了,政府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这似乎和美国人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是否比美国政府对于美国人来说更值得信任?也正是因为在这种心态之下,房价自然是不跌只升的,因为不管以什么不合理的价格买下的房产都会有另一个对国家有信心的人来收走。此时,又变成了房地产的价值不是其内在真正的价值,只是被一帮子有信心的乐观主义者眼中的价值。不对,他们自己不需要是有信心的乐观主义者,只需要他们相信还有一帮子有信心的乐观主义者的存在!
- Traders and Market Makers
交易员的作用是使得市场更为有效、因此价格也更能体现真正的价值。但是人们对交易员的意见在于,这些交易员往往不是为了使得市场更有效而工作,而仅仅是为了在交易中取得自己的利益。能否取得利益取决于交易员是否能在这场交易赌博中的赌技,但是因为而受到危险的赌博筹码却不是交易员自己口袋里的钱。交易员业界的共识似乎是,所谓的交易的专业就在于如何占到便宜,并且他们自己对此不愿多谈,那自然会引起外部的种种不满。
有一种理论称,市场和交易的关系可类比于人身上的多巴胺,多巴胺是人脑的一种分泌物,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多巴胺系统面对信号的反应是它接受突出的信号,如果该信号和之后的实际情况一致那就不会发生什么,如果信号和之后的实际情况不一致,那么则会降到不寻常的低值。市场对信息的反应也是如此,往往是在发布发放利息的时候股价会有反应,反而在真正发放利息的时候反应平稳,如果真正发放利息和之前预报的不一样,那反应会变不寻常。
经常会听到人们反对衍生市场的发展,人们往往对这种关于物价、GDP、房地产的衍生市场交易的运作有抵触情绪,觉得这种交易其实是给投机取巧的人制造机会。但是人们却丝毫没有想要伸张关闭现有的股票或债券市场交易的想法。其实它们本质上都是交易,差别仅仅在于人们似乎倾向于认为衍生市场的交易容易引发道德问题,但是真正导致问题的是没有好好掌控风险。
- Insurers
关于保险业,作者从BP在2010年的一次石油泄漏说起,他觉得媒体夸大了这次泄漏的损失,但是事实上这起事故大部分的损失都被保险包含了,唯一最大的损失是那些因此事故而丧生的船员。保险的作用,听起来似乎有讽刺意味,在于不管什么事故损耗都不会有太大影响,只要不是那种全球性的大灾难。保险的民主化,是使更多的大众能够享受到保险的服务,而这种保险应当是简单明了的。保险的人性化,是能够为人们的一些长期的困扰做保险,比如生命、健康等等。
说到保险业,我想到的竟然是碟形世界里的Twoflower – -|||
- Market Designers and Financial Engineers
市场设计师,是指通过设计市场和相关交易合同来解决普通人遇到的实际的窘境。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做媒服务,这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和财务金融相关的事情,但是有报导指出人们之所以单身,其实并非因为很难碰到其他单身的人(单身对方的供应量不小),而是因为他们很难判断他们所期望的对方身上的品性的供应情况,这就很显然是市场设计师可以帮忙的地方。
- Derivatives Providers
衍生产品,在现在听起来几乎是一个贬义词。所谓的衍生产品,包括期货(在现在设定未来某日交易的价格)和期权(在现在交易的在未来某日或某日之前以设定价格出售或者买入的权利)。据说最早的衍生产品的例子,是公元前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为了证明哲学家也能赚钱而创造的。泰勒斯付了一笔钱,得到在收获后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橄榄的权利,然后橄榄大涨,泰勒斯大赚。
在面对衍生产品的时候,特别是期权,我一直非常困惑。因为不管是call option还是put option,其实可以等同于购买这个期权的那方购买了一种保险,从而控制了一定的风险。但是问题是,这种风险的控制又和保险公司能带来的风险控制不一样,因为保险公司和保险购买者的利益并非是零和的,而期权的购买者和出售者的利益是零和的,那么如果期权的出售者和购买者一样聪明的话,他们怎么会答应这笔交易呢?市场上,哪里来的那么多愿意出售期权的人呢?
有研究显示,其实在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中,存在着种种非理性。如果说经济没有效率,那是因为缺乏风险的市场(没有人去评估风险)。照道理,衍生产品的市场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它其实是可以体现风险的价格的。而在现实中,参与衍生产品交易的人,往往并不是在想要控制风险,而是以为自己可以更好的预测市场而从中牟利。如果有朝一日,期权真的可以体现风险价值的时候,那么它将对整个好社会起到促进作用。
- Lawyers and Financial Advisers
随着机器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似乎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被机器或者计算机取代,但是那些需要思考和复杂交流的工作则很难在可预见的未来内被取代。律师和财务顾问就正好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们所具备的不仅仅是详尽的专业知识,还担负着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客户人性化交流的责任。现在有一些网站是提供机械化的财务顾问服务的,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些算法后面还是需要真正的财务顾问的支撑。法律和律师也是同样的道理。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是律师还是财务顾问,人数都很不充足,这就导致了往往只有已经很有钱的人才能享受到他们的服务。而法律和财务顾问的服务内容其实包括了帮助理解我们面临的金融世界,比如说房地产的抵押、信用卡的合同等等。这一缺口,部分地被金融产品的销售者填补了,但是还很不够。也有人争辩说,即便有了律师和财务顾问的帮助,他们未必也能不犯下类似造成金融危机的错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对这两个职业的发展(包括国家的补贴),来构造更好的财务资本主义。
我记得当年学西方经济学,说最基本的一条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然后才可能通过各种建模来理解经济。但是现在看来似乎这一假设即使成立也还是不够的,因为金融世界如此复杂,人们参与其中的互动也只有在理解它的前提下才显得有意义。就好像想要通过分析一个不懂围棋规则的人的下棋思路来赢棋是没什么意义的。在这里,律师和财务顾问扮演的应该就是规则解释者的角色。但是问题是,我们应该把规则简化到让参与的人单凭直觉(单凭“我是理性人”)就可以懂得的程度呢,还是根据需求把规则复杂化,而且多来接个规则解释者?
- Lobbyists
说客的作用,似乎可以通过向法律制定者游说,来对影响影响政府。从理论上来说,说客的存在是对金融社会有帮助的。因为他们代表了懂得市场和金融需求的那一方,他们的游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助政府和法律规则的制定者理解相关的专业情况。但是问题是,如果说这些说客存在的意义是能够使公共利益得到提升,但是他们的既得利益肯定不是为了这些。换句话说,他们通过游说而得到的为了自己或者所代表的集团的私利,肯定比真正促进的公共利益要高的多得多。
接下来的问题是,说客到底代表了谁?现在绝大多数的说客,是在代表各大金主,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是为了社会问题(比如同性权利或是堕胎权利)。不管是代表的行业团体,还是社会团体,这些说客们都拿着很高的报酬。也就是说,说客们代表的是那些有钱人的利益。那么说来代表没有钱的人来向政府和法律制定者表明自己的立场呢?最接近穷人的说客,那就是工会了。
怎样的人适合做说客?他们向政府呈现观点,其实就好像律师为客户辩护一样,谈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并不是那种道德观比较淡薄的人才能充当好一个说客。能成为说客的,要么是对公共事业感兴趣同时可以通过这个赚大钱的,要么是对政治感兴趣却不愿意承担做公仆的牺牲的。
说到说客,我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形象是《Thank You for Smoking》里的烟草协会的代言人,第二个是《House of Cards》里的Remy Danton。怎么想怎么都觉得是淡化自己的个人信仰、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来为付钱的雇主来通过影响政府进而操控市场的。但是作者这里把说客和律师做横向对比,我也觉得似乎没有错。我觉得这里的差别在于,被告与原告或者诉讼方的律师实力是均衡对等的,而说客这边的影响是单方面的,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 Regulators
监管机构是规则的制造者。但是对于大多数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存在感。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监管的规则是多是少,而在于这些规则的制订是出于谁的利益。根据作者的亲身经验,他发觉这些在监管机构里工作的人,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无能。
-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
会计是从财务的角度来记录一家企业,审计则是来评估和解释会计的工作。会计和审计承担着维护财务结构完整正直的责任。如果说CEO是人脑中的中枢神经的话,那么会计就是海马体,把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连接各个记忆。会计往往应该站在稍远的地方,不能被CEO操控。
- Educators
财务知识领域的教育者,承载着相当微妙的作用。作者认为,近年来有效市场的理论对于学生来说有点过度教育了。因为对有效市场的坚定不移的认识,很多人以为不管是否是有道德地行事,都不会影响市场,因为有效市场终究是平衡的。因此也就帮助造就了很多泡沫。
- Public Goods Financiers
公共事务与私有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公共事务并不由自由市场所支撑,它是尾所有大众服务的,同时它是政府存在的最主要的理由。但是公共事务的影响和结果,却很难被看见、也很难被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为政客投票的人,是在衡量着什么才决定选择的呢?就公共事务的发展,比如关键的点子未必是政府想出来的,或者政府可以去资助某些组织而不是简单地雇佣公务员来处理公共事务。
- Policy Makers in Charge of Stabilizing the Economy
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是制定政策,来对抗不稳定因素、减小不稳定带来的影响。但是问题是,事情的缘由是很复杂的,是多因素的。去分析它/预测它,往往不仅仅是数学层面的,而且是需要人为的判断的(其中包括对政治气候、社会氛围的判断)。
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大型的变迁,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设立一些金融产品来自动稳定。比如说失业保险、分阶所得税,再比如政府发行基于自己国家GDP的股权。
- Trustees and Nonprofit Managers
信托和非营利管理者和别的组织最大的不同是它们的诉求,因为它们的诉求往往是更高层面。信托的特点在于它的长久性,它的建立本身就是为了可能是建立者生命长度之外的作用。非营利,并不是指不赚钱,只是指不向股东发放红利,它们的目标就不在于寻求最大的投资回报,而在于追求某种目标。
- Philanthropists
《小王子》里面小王子问商人:“拥有星星有什么好的?”商人说:“这能让我变得富有,就可以买更多星星。”这是连小孩动能读懂的道理:拥有东西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更是如此,所谓的慈善家就是赚钱来发派给别人以支持他们追求特定缘由的。有一种观点说,那些在商界成功的人,未必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要多聪明多少,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正好拥有能使得他们在商场上赚到钱的那些才能。他们在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以后,还是想要用这些钱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