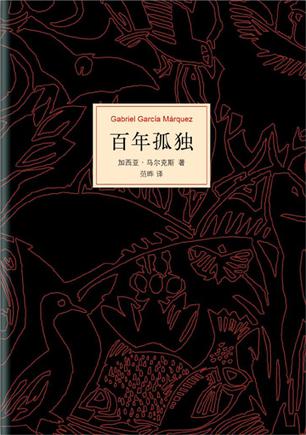 |
百年孤独 Cien años de soledad 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N/A(译) |
久负盛名的作品,去年才有正式中国版权出版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年孤独》,在开始读之前完全想不到原来是这么一部作品。我的感觉,就是在看一部跨越时间很长长达一百年的连续剧。当然这部连续剧是挂着“魔幻现实主义”的牌子的,其中的诸多故事也是很明显有着种种影射现实的隐喻的。
先讲两个杂七杂八的吐槽。这个家族的命名法也太缺乏词汇量和想象力了吧。第一代的男的叫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儿子叫霍塞·阿卡迪奥、孙子叫阿卡迪奥、曾孙叫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全家族6代人里面,有超过20个人都叫奥雷良诺。没有一张家族系谱真的有点难不搞混其中的人物关系,但是一旦看了网上好心人做好的人物族谱,就等于直接看到了这个家族一百年兴衰的结局,瞬间就剧透到底了。
说到剧透,其实最大的剧透家就是作者本身。因为作者非常喜欢用“某某在干嘛干嘛,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干嘛干嘛”或者是“当某某在二十年后干嘛干嘛的时候回想现在他干嘛干嘛”之类的句式。因为对于作者而言,他是全景视角,一百年内所有人的命运他都自己清楚。而读者还在乖乖看一个人少年时代的事情的时候,就直接被作者剧透说他老了以后会咋样咋样,有种说不出的宿命的感觉。我个人觉得,其实以情节为重的叙事类的小说,有一点像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较量。要是以顺序讲故事,故事讲到一半,读者就猜出了主人公后面的结尾,那作为作者就弱暴了。而马尔克斯所做的,就是在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趁着还没有给出足够多的线索的时候,就直接说出来这个人物的最终结尾,太赖皮了。
然后回到这本书的内容上来,我觉得这个家族真的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家族,人与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又都截然不同。光是凭作者可以创造出如此一个众生相的故事来,这就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具体的人物分析,我也不高兴一个一个地做了。反正我的总体感觉就是这些人都是在默默与生活在斗争的,不管是以何种方式,战争也好、情欲也好、斗鸡也好、吃土也好、编裹尸布也好、升天也好。但是与他们的命运紧紧相联系的,却还是难以抹去的孤独。最令人回味的,还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我看的版本是这样翻译的:
这手稿上所写的事情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重复,因为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决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呢?我刚读完的时候没有理解,现在也不确定我的理解是对的。首先,我觉得所谓的“孤独”有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孤独,就好像书里面的人物,最明显的比如上校或者是他那织裹尸布的妹妹,当然还包括里面几乎所有的人。第二层我是从这个词本身想到的,这个词的西语原文是soledad,我猜对应英语的solitude。对于solitude这个词,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我总觉得solitude和solid是有渊源的,而solid引申出去还有solidarity这个词,明明看上去是从一个词引申出去的,怎么会有“孤独”和“团结”这两个似乎完全相反意义的词呢?后来,我想其实还是说的通的,所谓的团结是指内部的,如果把这个内部打包成一个整体,那它还不是相对除它以外的事物是孤独的吗?这里我说的第二层的意思,我猜是不是指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一整个家族,相对于外部的人也好,或者是外乡人也好,都是孤独的。因为似乎的确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像这样的家族,可能理解这个家族其错综复杂的真正的实质。那么作者在写下这一结尾的时候到底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的呢?他是觉得这样是件好事呢还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呢?我觉得肯定是偏向于后者的。并不是要说孤独什么的一定是一件好事,但是一个有意识地跟孤独打交道的家族、一个明白自己和孤独的关系的家族,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东西的缺失,在我看来,是一种遗憾。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似乎又能和马尔克斯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接轨。个人是孤独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一整个家族是孤独的,那么自然拉丁美洲也是孤独的。我觉得马尔克斯的这段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特别好,摘抄一段,用的是豆瓣某翻译文本。
我敢说更值得瑞典文学院关注的应当是这样一些惊人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这些现实并非只存在于作品的描述中,它们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决定着我们每天能看到的不计其数的死亡瞬间。它充满伤感,但又美丽异常,丰富滋养了我们的创造力之源。凭借着这创造力,我这个漂泊怀旧的哥伦比亚人靠着运气仅以一票之多而获奖。但不论是诗人或是乞丐,音乐家或是预言家,武士或是恶棍,亦或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生活的芸芸众生,我们无需有太多的想象力。因为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让别人相信我们生活的真实状况。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之病的症结所在。
如果那些有着相同本质的困难险阻妨碍了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世界的另一端的本土文化领域中广受称赞的人才们为何竟找不到解读我们的合理方式。他们利用他们衡量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于是那种误解现象就变得再自然不过了。但他们忘却了每个人生活中的不幸都并不一致,我们对自我本性的探求也同样历经艰辛。用不适合我们的方式来解读我们的现状只能使我们变得更不为人所知、更不自由、更加孤独。敏感的欧洲人如果把我们置身于他们历史上曾有过的处境里,也许会更容易理解我们。只需回想一下,伦敦花了三百多年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又花了三百年才成为一个有主教的教区;罗马人在黑暗和困惑中苦苦挣扎了二十个世纪,才迎来一个巩固其历史地位的伊特拉斯坎王。而今天以清淡的奶酪、精确的钟表,又崇尚和平闻名于世的瑞士人,直到十六世纪还在为掠夺财富在欧洲大陆大肆屠杀。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该国军队的一万二千名雇佣军还洗劫并毁坏了罗马城,杀害了八千多居民。
我无意引用53年前托马斯·曼曾在这里颂扬过的托尼奥·克罗格(Tonio Kröger ,托马斯·曼发表于1903年的小说Tonio Kröger中的同名主人公)关于将纯洁的北方和热情的南方融为一体的幻想。但我确信:包括在座的各位,所有那些为一个更人道的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如果考虑一下看待我们的方式,也许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只要孤独还未被转化成一种具体的法律去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各地都会有自己一席之地的人,伴随我们梦想的孤独就依旧会使我们感到孤立无助。
拉丁美洲既不渴望,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小卒。也不该一厢情愿地希望西方人也像我们一样如此渴求自立和创新。然而大大缩短了欧美间距离的航海的发展却反而加大了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当我们艰难地尝试社会改革时,为什么不能利用一下那种我们在文学创作中被慷慨赋予的创造力呢?进步的欧洲人可以把追求祖国的社会公正视为己任,而我们拉丁美洲难道就不能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吗?请注意:我们历史上所遭受的难以估量的暴行和痛楚都是长期以来不公待遇和难言的暴力统治造成的,而不是离我们3000里格远的人所设计的阴谋。但是许多欧洲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似乎忘记了他们年轻时创造的伟大成就,幼稚地认为除了在世界上两巨头的仁慈照顾下度日外没有别的出路。而这,朋友们,就是我们现在孤独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用生命来反抗压迫、掠夺和遗弃。无论是洪水或是瘟疫,饥饿或是灾难,甚至是年复一年永无休止的战争,都不能扼杀生命的力量,它永远比死亡强大。这种强势不断发展壮大:每年净增人口七千四百万—足足是纽约人口的七倍。大多数新增人口出现在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拉美国家。而与此相反的是,世界上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已经积聚了可以灭绝生活在这个不幸星球上所有生物一百次的可怕力量。
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当年像我这样接受诺贝尔奖时说:“我拒绝接受这是人类末日的观点。”如果我还没能弄明白32年前他拒绝接受的那种巨大悲剧不过是自人类起源以来的一个简单的科学事实,我就会觉得不配站在这个当年他曾站过的位置上。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会被仅仅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令人畏惧的事实面前,我们这些传说的创作之人将愿意相信任何事情,并会感到现在开始去建立一个与现今事实相反的乌托邦还犹时未晚。一个崭新的无边界的乌托邦将会诞生。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决定别人怎么去死;爱情将成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而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将最终并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第二次机会。
2 Comments